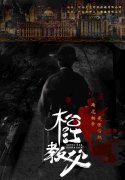借助青春面孔呈现革命英雄的叙事方式承袭了“新主流”大片的美学惯例,于是我们看到《觉醒年代》中张晚意饰演的陈延年、马启越饰演的陈乔年,《革命者》中章若楠饰演的李星华和《1921》中刘昊然饰演的刘仁静(顺时针方向)等,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这一美学范式在“建国三部曲”当中的具体呈现方式则是“全明星阵容”: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到《建军大业》,每部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位明星出演,呈现出年轻化、偶像化的趋势。普通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享受到“数星星”的快感,更有不少粉丝由于偶像的出演而走进影院。彼时的偶像明星不仅是票房的保障,更是观影快感和认同感的载体。偶像明星的出演建立起有效的认同机制,对于成长在时代红利当中的“90后”“00后”而言,虽然革命经验遥远而陌生,但通过这套机制,他们仍然能够经由认同偶像而认同其扮演的历史人物。
青春编码的新阶段,其突出特点在于青春之于史实和作品的内生性,通过人物形象传达的朝气蓬勃时代精神与国家形象
不妨将建党百年之际涌现的这一批佳作看做是主旋律影视剧青春编码的2.0时代。如果说主旋律影视的新主流转向是与粉丝文化、明星工业等消费主义话语博弈的结果,那么从1.0时代“谁红谁演”到2.0时代“谁演谁红”,则折射出博弈过程中力量对比的变化:迭代之后的主流叙事形成了青春编码的新语法,对消费主义话语从倚重到独立,甚至大有反向输出的趋势——演员由“青春之国家”和“青春之我”而获得“灵韵”或者说魅力,在剧集“破圈”的同时演员的口碑和商业价值得到极大提升。
崭新的叙事语法与Z世代产生共鸣
其次,对演员来说,剧作在艺术和技术方面的成熟对演员的表演提出更高的要求,也为演员塑造角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
青春编码的迭代升级,一方面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扶植和艺术创作者的孜孜求索,另一方面则根源于受众需求的转变。1.0时代的青春肉身激发了受众对主旋律的兴趣、培养了观影习惯,是审美积淀的过程,由此观众的审美品位得到提高,“拼盘式”和“数星星”式的快感不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这是编码迭代的审美动因。而疫情带来的国内国际局势的历史性变化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同时“福报”制工作状态、“内卷”化生存环境等社会问题,如周展安指出,加深了年轻人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也萌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兴趣,1.0时代单薄的叙事和人物难以言说更加深刻的体验、情感与思考,这是编码迭代的社会动因。由于审美和社会的共同助推,主旋律影视剧由探索走向成熟,呈现出崭新的美学面貌。在以《1921》《革命者》《觉醒年代》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主旋律影视作品当中,艺术性、思想性、娱乐性和商业性得到了很好的平衡,主旋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或许我们可以说,青春编码向2.0时代的升级也同时意味着中国的主旋律影视剧由此进入意气风发的青春岁月。
在新一代主旋律影视作品当中,艺术性、思想性、娱乐性和商业性得到了很好的平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如果将“建国三部曲”看作主旋律青春化探索的1.0阶段,那么《觉醒年代》在今年的热播让我们欣喜地看到青春编码的新阶段,其突出特点在于青春之于史实和作品的内生性。《觉醒年代》的青春并不完全意味唇红齿白的偶像演员和风华正茂的历史人物,更是通过人物形象传达的朝气蓬勃时代精神与国家形象。全剧以《新青年》杂志的创业史为主要线索,勾连起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与“建国三部曲”不同, 《觉醒年代》的情节更加丰满、人物更加立体,更重要的是类型元素并没有喧宾夺主,而是烘云托月般地突出全剧的主角——年代。古老中国在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潮的动态角力当中逐渐觉醒,开始焕发出勃勃的新生机。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论是中年的陈独秀、章士钊,青年的李大钊、胡适、毛泽东、周恩来,还是少年的陈延年、陈乔年,甚至是年逾不惑的蔡元培,所有人物的行动统摄在为中国寻找出路这样一个大理想之中,共享着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澎湃激情。这样,个体成长与国家新生之间形成同构关系,既摆脱了浪漫主义叙事,又没有落入人道主义家庭伦理剧的窠臼,而是将个体叙事嵌入国家叙事,个体的热血求索既讲述着时代的觉醒,又塑造着国家的青春形象。

 图片中心
图片中心